郑大七年致力培养人才(七)
来源:潍坊晚报 发布时间:2023-05-20 17:1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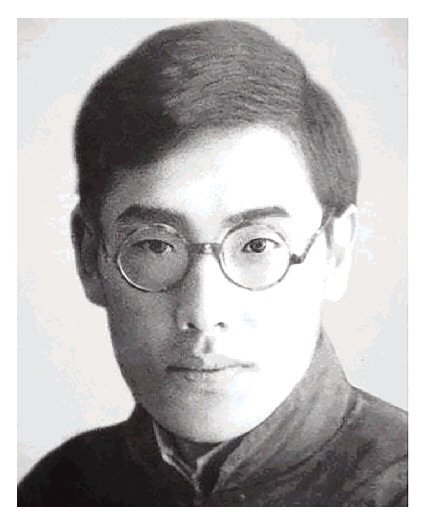
青年赵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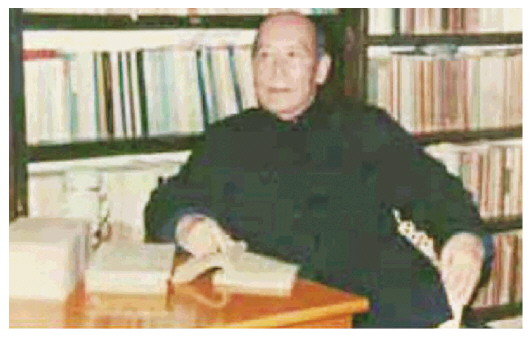
韩连琪
从1978年到1985年,秦佩珩在学术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郑州大学取得了明清经济史的硕士授予权,他开始培养后继人才。此阶段,他继续城市经济研究以及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有关治学方法的研究文章,他提出的观点,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革”期间劳动改造
学生风尘仆仆探望
在“文革”期间的情况,当时秦佩珩的学生孙宪周这样回忆道:
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也在一个中学里被打成了“走资派”……先生朝不保夕,却仍然惦记着我,多次来信询问情况,我为了不连累先生,很长时间不去拜访他,但内心也在惦记着先生。1969年,先生全家随同历史系,被下放到郾城县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先生由于长期受折磨,心脏就有了衰弱的征兆。我担心先生体力吃不消,又担心全家老小,久住城市,如今下放荒村,能否习惯。我便乘车去漯河,然后步行几十里,到了先生劳动的郭寺村。先生见我风尘仆仆而去,跑上前去,紧握我的双手,连连摇晃,好久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也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如同经历了大劫大难侥幸不死,又见到了亲人一样,我和先生都高兴极了,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因为当时正开展大批判,老师们都在紧张地写批判稿和大字报,我假期有限,便于第二天早饭后告别先生。先生一直送我到村头,留恋之情痛彻肺腑。我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归程,走了很远,再回过头来,先生还站在村头望着我……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象更新。这对于秦佩珩而言,也迎来了新生。后来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中写道:“拨乱反正以后,我每出外经郑州换车,必到郑大;每到郑大,必先趋秦府。佩珩不爱修边幅,满口安丘乡音,豁达不拘小节。有一次他高兴地说:“囔咱安丘出了不少史学家啦。你是一个,韩连琪是一个,我也算一个,这不就仨啦嘛。”
克服困难为国家培养接班人
从1978年到1985年,在这7年间,秦佩珩在学术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此时,郑州大学取得了明清经济史的硕士授予权。秦佩珩开始逐渐培养后继人才。他认为:“在业务上的发展,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提供了可靠保证。从1978年开始第一批,从1982年开始第二批,从1985年开始第三批。希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尽管自己在许多问题上遇到严重困难,但努力克服,相信会使工作继续保持下去。”
也正是像秦佩珩一样的老师在此任教,不断努力,使得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以来,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嵇文甫、荆三林、史苏苑、刘铭恕、张文彬、高敏、戴可来、李民、杨天宇、袁祖亮、郑永福等国内知名学者曾在此执教,传承了优良的教风和学风。
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
秦佩珩在科学研究上,一是继续城市经济的研究,包括古代和近代的,也包括理论阐述和调查考据。他先后写了许多这类文章,如《邺城掇琐》《金都上京故城遗址沿革考略》。
二是继续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他先后写了一些文章:《明代治河史札》《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明代蒙汉两族贸易关系考略》。
此外,在治史理论和方法方面,他写了《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对于史学研究,他主张:“文必有益于世,治学领域必须扩大和结合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来研究,否则穿旧鞋走老路是没有前途的。”
他还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针对西南的白族写成《试论南诏史的研究》《关于南诏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等。1979年第三期的《求是学刊》发表了秦佩珩的《必须加强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文中认为全面系统地整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是十分必要的。无视或轻视对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研究,既不符合我国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团结。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是摆在史学、经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文中还指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或经济史,也应遵循客观规律。在研究边疆各族社会经济史的时候,必须重视资料的研究,从大量可靠的资料中,如实认识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过程,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治学上提出新观点
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秦佩珩还有一些研究文章是偏重于专谈治学方法的,例如:《史海夜航》《史舟习驶》《史苑窥管》(《在茫茫的学海中》)等文章。在《史海夜航》中,他提到:“一个经济史工作者,必须刻苦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得愈深愈好。不是简单地引用词句,而是把精神实质贯彻、渗透到我们要表达的经济史问题上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是中外进步的经济史学者所必须采取的方法”。
此外,还要必须重视史料的价值和作用。“史料工作是经济史研究阵线上的先行官”,他认为,“在治经济史方面,也有一个博与约的问题。博,意味着广大;约,意味着精深;能广大精深才算真正的专。治学不能博大精深,没有基础的专家是很可怕、很危险的。博和约,是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但到了一定条件下,两者又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做到相反相成。不博又怎能谈约,约从何起?不深又怎能谈精,精从何起?做到体大思精,方算得是专”。
在《史舟习驶》中,他提到了许多观点和想法。在经济史研究的选题问题上:要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处理好选题和现实的关系;要填补史学的空白,在做法上,要补史之缺,实事求是。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有较少经验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填补历史上的空白问题,不宜抓过大过宽的问题;而对于一个有较深修养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又不宜抓过小过狭的问题。在搜集和运用资料的问题上: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每个时代都会具有其一定典型资料的特征,而且资料的内容与形式也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整理经济史料时,应当充分认识到:无论内容与形式如何,都是由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观点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者,应当科学地选择某一主题的资料,并要求全面研究现有材料。
在《史苑窥管》中,他提出:治史,必须尊重史实,不能迎合某种需要,随意篡改历史,乱搞影射史学。同时他认为读书或撰文:视野要宽,信念要坚。由点到面,由博到约。如果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人就无法取得进步。
可以说,秦佩珩提出的这些观点,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邢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