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风录被誉现代诗三百
来源:潍坊晚报 发布时间:2022-09-12 17:5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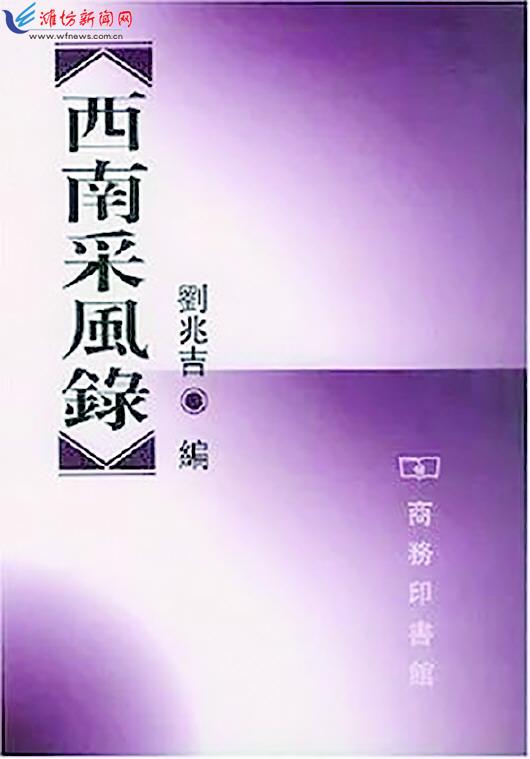
《西南采风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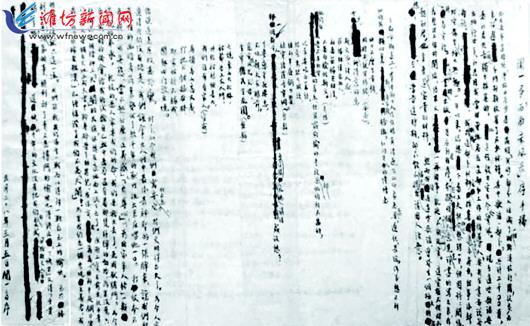
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言手稿
约在1939年春,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的编著工作,其中收集了771首民间歌谣,受到多名大师的赞赏。刘兆吉邀请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著名导师作序,三人均高度评价。然而就在1946年12月出版的4个月前,对这部采风录费心血最多的闻一多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完成采风录编著受三名导师称赞
从长沙到昆明,刘兆吉或深入村寨,或走进田间地头,或爬上云雾缭绕的山头,吃了更多苦,跑了更多路,锲而不舍地搜集山歌民谣。在两个月时间里,他共采集各类歌谣2000多首。经过分辨、整理,最后选出771首,按六大类排列:情歌、儿童歌谣、抗日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其中情歌占90%以上。
约在1939年春,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的编著工作。所选歌谣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表现出丰富的风俗民情和浓郁的地方色彩。这是中国第一部西南地区歌谣选集。手稿经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审阅,同时受到王力、罗莘田、赵元任等语言大师的赞赏。
刘兆吉邀请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著名导师作序。朱自清的评价极高。他认为,此举不同于传说中古代天子派使者乘着轻车到民间采集歌谣,而是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黄钰生对刘兆吉了解最多。他亲眼目睹了在湘黔滇三千里步行中刘兆吉采风的画面,“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青年,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本来,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学生,跑来问长问短,是稀有的事,是可疑的事——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他认为,《西南采风录》“是一宗有用的文献。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言;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
闻一多序言多赞赏肯定价值建议出版
闻一多对《西南采风录》所费心血最多。刘兆吉晚年回忆:“在两个多月、三千五百里路程中,我尽量争取机会向他请教。晚上在沿途山村农舍临时住宿地,与他讨论搜集的民歌。闻先生和学生们同样席地而坐,在菜油灯下,他忘了一天走80多里山路的劳累,高兴地审阅我搜集到的民歌。有时捋须大笑,赞不绝口。老师的期望和鼓励,使我干劲更大。”
闻一多在序文中,特别摘出6首歌谣,其中包括他和刘兆吉发生争论的那几首。这几首歌谣字面上看粗犷、豪放,也确如刘兆吉最初的认识,“原始、野蛮,似乎是在歌颂土匪强盗”,然而闻一多却透过字面看到了更深层的内涵,体察到了更重要的精神,因而他要把这“极大的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对闻一多来说,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自信,而他的自信,也有从这些看似“原始”“野蛮”的山歌民谣中得到的极大启示。他在序文中写道:
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西南采风录》,也正是在闻一多的提议下,刘兆吉才鼓起勇气将它交给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看了汇编的歌谣后说:“这些民歌不但在民间文学方面有欣赏和研究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也很有参考的价值。要编辑成书出版呀!不然就辜负了这些宝贵的材料。”闻一多更赞赏刘兆吉不怕困难、坚持沿途采集山歌民谣的毅力。他写道:
正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
刘兆吉回忆说:“闻先生主动指导编选我采集的民间歌谣,并定名为《西南采风录》。在整理过程中,闻先生不厌其烦地以他渊博的语言学、音韵学知识,解决了许多疑难。”
新书出版思闻师序言手稿幸留存
由于当时处于国难时期,《西南采风录》一直拖到1946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刘兆吉已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
“当我拿到新出版的《西南采风录》时,片刻的喜悦,就被刺心的悲痛压抑了。因为闻师就在此书出版的4个月前(1946年7月15日)壮烈牺牲了。这是凝结着一多师心血的书呀!我捧着新书哭了!泪花中映着闻师迈着大步跨越在云贵高原山路上的身影和上课谈话时的音容笑貌。但已听不到他关心的这本书出版的喜讯了。”
刘兆吉决定将稿费全部献给闻师母。他写信给朱自清先生,表达了这一愿望。朱自清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梅贻琦校长等人很关心闻师母及其子女的生活,已安排闻师母到图书馆工作,一家生活还可维持。又说刘兆吉,“你已是五口之家,一个中学教员,经济上也不宽裕”,劝刘兆吉不必寄钱,但会把他的善意转告闻师母。
《西南采风录》出版后,联大师生争相传阅,誉为“现代诗三百”。至今已有国内外多种版本,影响深远。然而,刘兆吉儿子刘重来家里却仅有一本原版书,还是刘兆吉的亲哥哥留给他的。这位亲哥哥当初辍学去药厂当学徒,后来参加了革命,当了八路军野战医院的院长。解放后,在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1949年,哥哥偶然在苏州商务印书馆分馆看到弟弟的书,非常高兴,当即买下,并自豪地向朋友们宣传。“文革”开始后,刘兆吉被反复批斗、抄家,其中一个罪状竟然是“游山玩水”,说的正是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许多资料有去无回,《西南采风录》也未能幸免。幸好哥哥没有受到冲击,得以留下这本珍贵的原版书。
被抄家时,书中掉出一些破旧的纸片没有被拿走,就包括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于1939年给《西南采风录》作序的手稿。战时艰苦,这些序言都写在很差的土纸上。如今,在云南师大内的西南联大博物馆,这三份珍贵手稿的复印件被裱在镜框中,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
责任编辑:邢敏